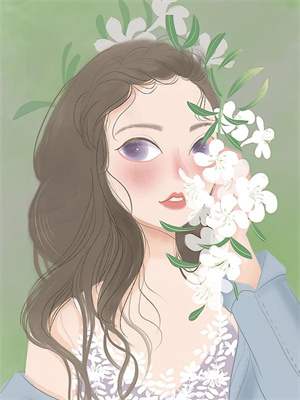简介
《大理寺异闻司》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悬疑脑洞小说,作者“穆王八骏”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,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。小说的主角沈墨阿箐勇敢、善良、聪明,深受读者们的喜爱。目前,这本小说已经更新总字数287295字,喜欢悬疑脑洞小说的你快来一读为快吧!
大理寺异闻司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孙槐之死,如同在京城看似平静的湖面下,引爆了一颗无声的惊雷。消息虽被大理寺与刑部联手严密封锁,未在市井间掀起波澜,但在那朱墙内外、权力中枢的特定圈层里,该知道的人,都已于第一时间知晓,并迅速做出了各自的判断与反应。
刑部一名虽品级不高、却身处关键位置的书吏在家中被离奇灭口;大理寺深夜突击搜查背景复杂的瑞昌号银楼;齐王名下关联产业福瑞轩的掌柜被公然拘传……这一连串发生在短短十二个时辰内的激烈事件,如同一把无形的锹,狠狠搅动了朝堂之下原本就暗流涌动的污泥,让本就微妙的平衡瞬间被打破,空气中充满了一触即发的火药味。
齐王府首先做出了反应。然而,并非众人预想中的激烈弹劾或公开施压,反而是一种更隐晦、却更具压迫感的沉默。齐王李玠以“感染风寒,需静心休养”为由,连续三日未曾上朝,其门下官员、依附派系也仿佛接到了统一指令,在朝会之上骤然变得异常低调,对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议题都三缄其口,不再发声。但这种异乎寻常的、带着刻意的沉默,反而像一块不断积聚、沉重无比的乌云,低低地压在每一个密切关注此事进展的官员心头,预示着更猛烈、更不可测的风暴正在酝酿。
与此同时,一道来自宫中的申饬谕旨,越过层层衙门,直接落在了大理寺卿的案头。旨意措辞罕见地严厉,直指大理寺办案不力,举措失当,致使重要人证孙槐于关键时刻死于非命,严重阻碍案情侦办,责令限期破案,务必肃清奸佞,以正国法。但在这严厉的斥责之后,谕旨末尾却笔锋一转,意味深长地添上了一句:“然亦须明察秋毫,不得妄加牵连,动摇国本,徒惹朝局不安。”
“不得牵连无辜,动摇国本……”周淮安在异闻司的值房内,将那份质地考究、字迹却冰冷刺骨的中旨轻轻放在紫檀木案上,指尖在“国本”二字上重重一按,嘴角泛起一丝带着疲惫与讥诮的弧度,“沈主事,你可知晓,这谕旨中所指的‘无辜’与‘国本’,究竟是何人何物?”
沈墨垂首立于堂下,窗棂透过的光线在他清俊的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,他声音平稳,听不出情绪:“下官明白。宫中是在提醒我们,亦是警告,查案需把握分寸,懂得适可而止,切莫轻易将火引向齐王殿下,以免引发不可控的朝堂震荡。”
“是啊,齐王毕竟是陛下唯一的同母胞弟,血脉至亲,尊贵的亲王。没有如山铁证,动他,便不仅仅是触怒龙颜,更是动摇皇室根基,是为‘动摇国本’。”周淮安长长叹了口气,抬手用力揉着发胀的眉心,语气中充满了无力感,“如今孙槐一死,这条最可能直指核心的线索算是彻底断了。瑞昌号的账册又被焚毁大半,仅凭那些抢救出来的、指向不明州府的残缺页张,以及那个无人能解的古怪符号,根本不足以形成完整、闭合的证据链条,无法指证任何人。而福瑞轩那个钱德明,又是个油盐不进、忠心护主的滚刀肉……”
形势急转直下,似乎一下子变得对锐意追查的沈墨和背后支持的周淮安极为不利,前方仿佛已是山穷水尽之局。
“寺正大人,下官以为,线索并未完全断绝,甚至……因对方的激烈反应,反而变得更加清晰。”沈墨抬起头,目光沉静如古井深潭,却闪烁着不容置疑的洞察力,“孙槐之死,恰恰用最残酷的方式证明了我们之前追查的方向是正确的,并且已经触碰到了他们绝不愿暴露的核心区域。对方如此急于、敢于在京城之内行灭口之举,正说明孙槐掌握着足以致命的关隘信息。而瑞昌号残存账册虽不完整,但那个反复出现的诡异符号,以及资金最终流向所呈现出的特定规律,其本身,就是目前最宝贵、也最重要的线索!”
他稳步上前,将一份连夜整理、墨迹犹新的分析卷宗呈给周淮安:“下官与阿箐彻夜未眠,仔细核对了所有残存账目上的时间节点与流向记录,发现通过这些药材铺和道观作为中转站流转的巨额资金,无论起始路径如何迂回曲折,其最终指向,都惊人地汇聚向了一个共同的大方向——帝国西南边境诸镇。而且,在时间上呈现出极其明显的规律性,几乎都集中在每个季度的末尾进行集中划转。”
“西南边境?”周淮安神色骤然一凛,身体不自觉地坐直了,眼中充满了震惊与警惕,“那里临近狄人部落,虽近年无大规模战事,但小规模摩擦、冲突从未间断,局势向来敏感复杂。‘幽冥道’不惜耗费如此周章,将巨额资金秘密汇集到那里,他们……意欲何为?”
“下官大胆推测,”沈墨压低声音,语气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,“其目标,极可能与掌控边镇的实权将领有关。或是暗中资助、拉拢某些桀骜不驯、对朝廷阳奉阴违的军头,培植其私人势力;或是……更糟,直接与关外的狄人部落进行某种秘密交易,例如……军械、粮草,乃至情报!无论是其中哪一种,其心……皆可诛!”
周淮安闻言,猛地倒吸一口凉气,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,手指甚至因用力而微微发白。如果“幽冥道”的目标不仅仅是敛财自肥,而是进一步勾结外敌,祸乱帝国边防,那此案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!这已远超一般的贪腐渎职,而是危及王朝社稷安危的叛国大罪!其严重程度,足以掀起一场席卷朝野的滔天巨浪!
“此事……除了你与阿箐,还有何人知晓?”周淮安急声问道,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。
“回大人,目前仅下官与阿箐二人知晓。账目残破不全,信息记录又采用了极为隐晦的暗语代号,若非刻意寻找其背后隐藏的规律与共同点,极难发现其中奥妙。”沈墨如实禀报。
“好!此事到此为止,必须严格控制在最小范围,绝不可再对任何外人提及!”周淮安当机立断,语气斩钉截铁,他目光锐利地看向沈墨,特意强调,“尤其是秦王殿下那边,暂时……也绝不能透露分毫!”
沈墨心中微微一动,捕捉到了周淮安话语中那深重的顾虑:“寺正大人是担心秦王殿下他……”
“秦王殿下常年统兵,在边镇旧部众多,门生故吏遍布各大军镇,军中威望极高,甚至……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兵部。”周淮安意味深长地看着沈墨,声音压得更低,几乎细不可闻,“此事若与他无关,自然是朝廷之幸,万民之福。但若……若有关联,哪怕只是些许牵连,其后果……将不堪设想!在事情彻底查明之前,我们……不得不防。”
沈墨默然。周淮安的担忧不无道理,甚至可称得上老成谋国。秦王李琮有动机——扳倒齐王,扫清通往权力巅峰的最大障碍;他也有能力——掌控边镇,调动资源,与狄人建立某种“默契”或交易,从而制造紧张局势,凸显其不可或缺的军事地位,向朝廷、向陛下施压。这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测。
“那依大人之见,我们现在该如何行事?”沈墨将思绪拉回现实,请示下一步行动方向。
“明面上,”周淮安略一沉吟,迅速做出部署,“继续查办库银失窃案,但必须放缓节奏,甚至可以故意做出几分被宫中申饬后束手无策、进退维谷的姿态,以此麻痹对手,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已无力深究。暗地里,集中所有绝对可靠的人手,放弃其他枝节,秘密且全力调查两件事:第一,那个符号的确切含义与来源;第二,这些资金最终在西南边境的具体落点与接收对象!”他顿了顿,眼中闪过一丝决绝,“我会动用一些……不为外人所知的特殊渠道,设法帮你查探边镇那边与此相关的异常动向。”
就在此时,一名周淮安的心腹差役未经通传,步履匆匆地低头进来,行至近前,低声快速禀报:“寺正大人,沈主事,秦王殿下府上长史亲自前来,递送了一份请柬,邀沈主事明日午后再赴王府一叙,说是……殿下新得了些极品的雨前龙井,特邀沈主事一同品鉴。”
又来了!而且是在这个风声鹤唳、各方神经都高度紧绷的敏感时刻!
沈墨与周淮安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,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掩饰的凝重与警惕。
“看来,我们这位秦王殿下,对此案的‘关心’程度,远超你我的预料啊。”周淮安挥退差役,语气平淡,却字字千钧,“去吧,沈主事。既然殿下相邀,推脱反而不美。正好,也可借此机会,再探一探秦王的真实意图与口风。”他目光深沉地注视着沈墨,再次郑重叮嘱,“记住,谨言慎行,步步为营。西南边镇之事,符号来源之秘,绝不可在他面前显露半分。”
“下官明白。”沈墨躬身领命,心中那根弦已然绷紧到了极致。
次日,沈墨再次踏入那座气象森严的秦王府。与上次临水赏梅的闲适氛围截然不同,这一次,连引路侍从的脚步都显得格外沉重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、令人呼吸困难的肃杀与紧迫。秦王依旧在那间暖阁接待他,但眉宇间往日那几分刻意展现的平和已荡然无存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居上位的威压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。
“沈主事,坐。”秦王没有多余的寒暄,甚至未看一眼内侍奉上的香茗,直接切入正题,声音低沉而带着压迫感,“听闻刑部那个叫孙槐的书吏,死了?瑞昌号,也被你们大理寺连夜抄查了?”
“回殿下,确有此事。是下官部署不周,行事不密,未能保护好关键证人,致使线索中断,请殿下责罚。”沈墨依礼坐下,姿态恭谨,言辞谨慎,将责任先揽到自己身上。
“责罚?哼,”秦王从鼻子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,眼中寒光乍现,如利刃出鞘,“非你之过,是对手太狡猾,也太狠辣!为了保全自身,竟敢在天子脚下行此灭口勾当!”他语气一顿,目光如炬,紧紧锁定沈墨,“齐王兄这次,为了撇清自己,可是下了血本了。断尾求生,弃车保帅,这一手,他玩得倒是愈发熟练了。”
他依旧毫不迟疑,将矛头死死对准齐王。
“殿下,目前……并无任何直接证据,可以证明孙槐之死与齐王殿下有关……”沈墨依照既定策略,试图维持表面的客观与审慎。
“证据?”秦王猛地打断他,嘴角勾起一抹充满讥讽与戾气的冷笑,霍然起身,“有些事,根本不需要那些繁琐的所谓‘证据’!孙槐为何早不死晚不死,偏偏在你们查到福瑞轩、即将触及核心之时突然横死?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杀人灭口!这,就是最直接、最残酷的证据!”
他几步走到沈墨面前,高大的身影带来强烈的压迫感,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依旧端坐的沈墨,话语如同重锤,一下下敲击在沈墨的心防上:“沈墨!我知道你心有顾虑,行事讲究章程律法!宫中的那份申饬,我也已然知晓!但你要明白,除恶务尽,姑息养奸!若因一时之顾忌,一念之仁慈,而放纵此等国之蠹虫、社稷大奸,待其缓过气来,重整旗鼓,将来必成倾覆我朝之心腹大患!齐王在朝中、在地方经营多年,党羽门人遍布天下,盘根错节!若此次不能借此良机,一举将其扳倒,等他缓过这口气,回过神来……你,我,所有参与此事之人,都将死无葬身之地!”
他的话语充满了极强的煽动性与不加掩饰的威胁,仿佛沈墨若不立刻明确站队,与他同心协力、不惜一切代价将齐王置于死地,便是自取灭亡,便是王朝的罪人。
“殿下息怒。”沈墨垂下眼帘,避开那过于锐利逼人的视线,声音依旧维持着固有的平稳节奏,“下官职责所在,必当竭尽全力,查明案情真相,使罪魁祸首伏法。只是,正因此案牵涉巨大,更需遵循律法,讲求真凭实据,尤其是涉及天潢贵胄,尤需慎之又慎,方能不负圣恩,不违律理。”
秦王死死盯着他,那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头骨,看清他脑中真实的想法。阁内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,只有炭盆中银骨炭偶尔发出的轻微“噼啪”声。良久,秦王紧绷的面容忽然松弛了几分,语气也随之一转,变得缓和了些许,甚至带上了一丝看似推心置腹的意味:
“也罢。本王知道你的难处,周寺正……想必也有他的考量。查案之事,你且按部就班,依照你们大理寺的章程去办。”他话锋微转,伸手拍了拍沈墨的肩膀,力道不轻不重,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味,“不过,记住,若在查案过程中,遇到任何难以逾越的阻碍,或是需要某些……特殊助力之处,尽管开口。本王,定当鼎力相助。”他微微前倾,声音压低,每个字都清晰无比地传入沈墨耳中,“记住,沈墨,本王,永远站在维护朝廷纲纪、肃清奸佞的这一边。希望……你也是。”
离开那座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的秦王府暖阁,沈墨的心情非但没有因暂时过关而轻松,反而如同坠了铅块,更加沉重。秦王的态度变得愈发急切、强硬且不加掩饰,几乎是赤裸裸地要求他尽快将齐王的罪名坐实。这与周淮安要求暗中调查、谨慎行事、甚至要防范秦王的指令,形成了尖锐而不可调和的冲突。
他感觉自己正被两股足以搅动朝堂的巨力夹在中间,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,稍有不慎,行差踏错,便会被无形的漩涡彻底吞噬,碾得粉身碎骨。
回到异闻司那间略显偏僻的值房,阿箐早已等候多时,见他归来,立刻迎上,脸上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与凝重。“沈大哥,有进展了!”她压低声音,眼中闪烁着发现秘密的光芒,“我通过几个信得过的老江湖渠道,辗转打听,终于得到了一些关于那个‘藤蔓缠绕眼睛’符号的零星信息!”
“快说!”沈墨精神一振,立刻将所有纷杂思绪暂时压下。
“有几个年轻时常在西南一带走镖、如今已金盆洗手的老镖师说,他们依稀记得,在西南某些极其偏僻、几乎与世隔绝的古老村寨里,曾在祭祀山神或进行某种古老仪式时,于岩画、木雕或祭司的法器上,见过类似的图案。那些寨子里的老人,管那东西叫……‘千目之藤’!”阿箐的声音带着一丝因神秘而产生的微颤,“传说中,那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一种邪神标志,象征着它能窥见人心深处的一切隐秘,其藤蔓能穿透阴阳,连接幽冥之地,沟通亡魂!”
千目之藤?窥见人心?连接幽冥?
幽冥道!
这个名字,与这诡异符号的传说含义,仿佛一道撕裂夜空的惨白闪电,骤然劈开了沈墨脑海中积聚多日的重重迷雾!
这个潜藏于黑暗中的组织,不仅结构严密、资金雄厚、渗透朝堂,其最核心的深处,可能还信奉并崇拜着某种古老而邪恶的未知存在!他们所图谋的,恐怕绝不仅仅是世俗的钱财或权力那么简单!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,可能远比想象中更加黑暗、更加令人不寒而栗!
西南边境的敏感局势、古老邪神的诡异传说、庞大资金的秘密汇集、对朝堂权力的深度渗透……当这一切破碎的线索被“千目之藤”这个关键词串联起来时,指向了一个让沈墨脊背发凉、血液几乎冻结的可怕可能性。
“阿箐,”沈墨的声音因极度的震惊与警惕而带上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沙哑,他抬起头,望向窗外渐渐沉落的夕阳,那余晖在他眼中映不出丝毫暖意,“我们可能……真的在不经意间,捅了一个深不见底、蛰伏着无数毒蛇的马蜂窝。”
他猛地转身,快步走回案前,目光死死锁定在那张描绘着“千目之藤”诡异符号的宣纸上,眼神由最初的震惊逐渐转化为磐石般的坚定。
“通知我们所有绝对可靠的人,”他语速飞快,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,“暂停一切明面上的调查活动,所有已掌握的线索,全部封存归档,对外只宣称案情陷入僵局。从此刻起,我们所有的力量与行动,要完全、彻底地转入地下,转入暗处。”
他略一停顿,眼中闪过一丝计算的光芒,补充道:“另外,想办法,疏通狱中关节,我要再单独见一次福瑞轩的钱德明。或许……是时候该让他知道一些,他那位‘神秘东家’可能并未告知他,甚至会让他感到恐惧的‘真相’了。”
引蛇出洞之后,或许该尝试……攻心为上。在这盘错综复杂、杀机四伏的棋局中,他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,哪怕……是从最细微的裂缝开始。
—
(第六章结束)
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