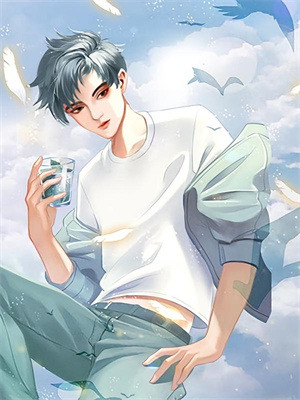简介
天汉血鉴是一本备受好评的历史古代小说,作者善行天涯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,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。小说的主角刘彻卫子夫卫青霍去病勇敢、善良、聪明,深受读者们的喜爱。目前,这本小说已经连载引人入胜。如果你喜欢阅读历史古代小说,那么这本书一定值得一读!
天汉血鉴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第八章:独尊儒术
建元元年(前140年),冬,长安,未央宫前殿。
寒风呼啸着穿过未央宫巍峨的宫阙,卷起殿前广场上的细碎雪粒,打在朱红色的廊柱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殿内却温暖如春,巨大的铜兽炭炉里,上好的兽炭无声地燃烧着,散发出松木的清香。文武百官分列两班,肃穆无声。年轻的皇帝刘彻,身着玄色十二章纹冕服,端坐于高高的御座之上。他十六岁登基,脸庞犹带少年意气,但那双深邃的眼眸,已初具洞察人心的锐利和掌控全局的威严。登基伊始,年号“建元”,昭示着他革故鼎新、开创盛世的雄心。
然而,这雄心之上,始终笼罩着一层无形的、沉重的阴影——长乐宫的主人,他的祖母,大汉王朝真正的权柄执掌者,窦太皇太后。这位历经文帝、景帝两朝,垂帘听政近二十年的妇人,虽已双目失明,却仿佛能“看”透这未央宫的每一寸角落。她是黄老之术最坚定的信奉者,信奉“无为而治”,厌恶任何剧烈的变动,尤其是儒生们鼓噪的那一套“仁义礼智信”。
今日朝会,气氛格外凝重。刘彻深邃的目光扫过殿下群臣,最终落在了一位立于文臣班列靠前位置的中年儒生身上。此人约莫四十余岁,面容清癯,三绺长须,穿着浆洗得有些发白的儒生常服,在一众锦袍玉带的公卿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但那挺直的腰板和沉静的眼神,却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坚韧与执着。他正是广川大儒,闻名天下的董仲舒。
“董仲舒!”刘彻的声音清朗而沉稳,在寂静的大殿中回荡,“朕即位以来,夙兴夜寐,常思自上古圣王,治道兴衰之由,天命更替之理。汉承秦敝,凋敝之余,奉行黄老,与民休息,六十余年,稍得喘息。然匈奴寇边,诸侯枝强,法令不一,民生犹艰。卿学究天人,明于世务,今朕亲策于廷,望卿直言无隐,试言大道之要、性命之情、治乱之端,朕将亲览焉。(皇帝策问的开始,表明求治国之道的急切)”
这是皇帝亲自下诏举行的“贤良对策”,旨在遍求天下治世良方。刘彻的策问,包含了三个核心:天人之际的感应(天人感应)、治国安邦的根本(长治久安)、以及天下归一的路径(思想统一)。每一个问题,都直指汉帝国运行的根本逻辑。
瞬间,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董仲舒身上。有人期待,有人审视,更有人(尤其是一些信奉黄老的重臣)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与敌意。一个布衣儒生,也配在庙堂之上高谈阔论治国大道?
董仲舒深吸一口气,仿佛要将胸中蕴藏多年的经世济民之策尽数吐出。他上前一步,躬身行礼,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,如同珠玉落盘,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: “陛下垂询,臣虽愚陋,敢不竭忠以对?臣谨案《春秋》之中,视前世已行之事,以观天人相与之际,甚可畏也!”(以《春秋》为引,点明天人关系的敬畏) 他开篇便定下基调,直指核心——“天人感应”。这是他的理论基石。 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,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;不知自省,又出怪异以惊惧之;尚不知变,而伤败乃至。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。”(天降灾异警示君主) 他列举上古圣王治世则天降祥瑞,桀纣暴虐则灾异频仍的例子,阐述上天并非虚无缥缈,而是通过祥瑞灾异,时刻关注并警示着人间的君主。君主的德行,直接关联着天命的眷顾与否。
紧接着,他话锋一转,矛头直指汉帝国当前奉行的主流思想: “今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,指意不同,是以上亡以持一统;法制数变,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,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从矣!”(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的核心主张) 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!这八个字,如同惊雷,在未央宫前殿炸响!清晰、强硬、没有半分回旋余地!他要的不是兼容并包,不是百家争鸣,而是用儒家思想,彻底取代其他学说,成为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,以此统一思想,进而统一法度,使万民有所遵循!
殿内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。御史大夫直不疑(黄老派重臣)脸色铁青,须发微颤,忍不住低声斥道:“狂生妄言!黄老清静,乃治国圭臬,岂容尔等竖儒置喙?!”
董仲舒仿佛没有听见,他挺直脊背,目光灼灼地望向御座上的年轻皇帝,继续阐述他那宏大而缜密的构想: 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也!(大一统是宇宙根本法则)陛下承天景命,富有四海,当立大学以教于国,设庠序以化于邑,教化行而习俗美!(建立官办教育体系)举孝廉方正,纳贤良文学,使天下之士,皆出于儒门一途,夙夜匪懈以修仁义!(以儒家标准选拔官吏)更化!唯陛下更化!易其辙,改弦更张,兴礼作乐,明君臣父子之纲常,定尊卑贵贱之等差!(彻底变革制度)如此,则阴阳调而风雨时,群生和而万民殖,诸福之物,可致之祥,莫不毕至,而王道终矣!(描绘理想治世图景)”
他的话语,如同构建起一个宏伟的蓝图: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根基,以天人感应学说维系君权神授的合法性,通过罢黜百家消除思想杂音,建立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庠序的官方教育体系,用察举制度选拔儒家官员,最终实现一个尊卑有序、万民归心、天佑神助的大一统帝国!这蓝图的核心,是将君主置于“天子”的神圣地位,同时以“天意”(具体表现为儒家的道德规范)来约束君主的行为。
刘彻端坐御座,表面平静如水。但董仲舒的每一句话,每一个字,都像炽热的烙铁,深深印入他的脑海,点燃了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火焰——绝对的权威!大一统的秩序!不受掣肘的皇权!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,早已无法满足他开疆拓土、掌控一切的雄心。董仲舒的理论,为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武器和统治依据。尤其是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这简直是替他清除了思想领域的障碍!他需要一种声音,一种只属于他、只歌颂他的声音!一种能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、塑造所有臣民思想的“正声”!儒术,经过董仲舒的改造,正堪大用!
他的手指,在宽大的袍袖中,不自觉地屈伸了一下。他看向董仲舒的目光,已不仅仅是欣赏,更带着一种发现绝世利器的炽热。然而,年轻的皇帝深知,这把利器尚未开锋,前方横亘着巨大的阻力。
长乐宫,椒房殿(窦太后居所)。
与未央宫充盈着年轻帝王锐气的氛围不同,长乐宫的椒房殿(窦太后寝宫)弥漫着一种陈年的、沉重的、略带药味的檀香气息。殿内光线略显昏暗,厚重的帷幔低垂,器物古朴而巨大,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沉淀与权力的稳固。
双目失明的窦太后,端坐于铺着厚厚锦褥的坐榻之上。她穿着深青色绣凤宫装,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,布满皱纹的脸上,没有任何表情,如同一尊深潭。她的手指,缓慢而有力地捻动着一串光滑的紫檀木佛珠。她的侄儿,时任丞相的窦婴恭敬地侍立在下首,脸上带着忧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。殿内还侍立着几位德高望重的黄老学者,皆屏息凝神。
一名心腹宦官跪伏在地,正竭力模仿着董仲舒的口吻和语调,将未央宫前殿对策的情形,尤其是那句石破天惊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。他的声音在空旷而寂静的大殿里回荡,带着一种诡异的穿透力。
“……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……邪辟之说灭息……” 宦官模仿董仲舒的声音戛然而止,额头沁出冷汗,趴伏在地不敢动弹。 殿内死一般的寂静,只有窦太后捻动佛珠发出的轻微而规律的“咔哒”声,仿佛带着某种冰冷的节奏。
“哼!”一声短促而充满戾气的冷哼,如同冰锥般刺破了寂静。 窦太后捻动佛珠的手指猛地一顿! “好大的胆子!”她的声音并不响亮,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阴冷威压,仿佛来自九幽地府,“区区一个儒生,也敢妄言‘罢黜百家’?黄老之学,乃高祖皇帝立国之本,文景二帝奉行之宗!清静无为,与民休息,方有今日之喘息!他董仲舒是何居心?是要掘了我汉家江山的根基不成?!” 她枯瘦的手指猛地指向窦婴的方向,虽目不能视,其威势却让窦婴不由自主地躬身更低: “窦婴!你是丞相!朝廷养士,竟养出这等狂悖之徒?!还有那个赵绾、王臧(赵绾时任御史大夫,王臧为郎中令,皆为新锐儒臣),整日里撺掇皇帝搞什么‘新政’,立明堂、巡狩、改历法、易服色!花样百出,劳民伤财!这哪里是治国?分明是搅乱纲常,动摇国本!”
窦婴心中叫苦不迭。他虽位列丞相,又是窦氏外戚,但内心对黄老的僵化并非没有看法,对年轻皇帝的锐意进取也抱有一丝同情。然而,在姑母的滔天威势前,他只能唯唯诺诺:“太后息怒……董生狂言,实属悖逆……臣……臣定当约束赵绾、王臧等人……” “约束?”窦太后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,“哀家看,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!还有皇帝……”她的声音陡然转厉,“哀家还没死呢!这大汉的江山,还轮不到他一个人说了算!黄老之道,不容亵渎!告诉皇帝,他若还认我这个祖母,就立刻停了那些儒生蛊惑人心的勾当!否则……” 她没有说下去,但那未尽的威胁之意,如同实质的寒冰,瞬间冻结了整个大殿。窦婴和那些黄老学者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,汗毛倒竖。
未央宫,温室殿。
烛光摇曳,映照着刘彻年轻而紧绷的面容。他刚刚送走了一脸愁苦前来“传达”太后懿旨的丞相窦婴。窦婴带回来的话,字字如刀。 “陛下……太后震怒……责令……责令陛下即刻罢斥董仲舒,停止赵绾、王臧等人所议之‘新政’事宜……否则……恐伤天家亲情……”窦婴的声音充满了无奈和恐惧。 刘彻背对着窦婴,看着殿外沉沉的夜色,拳头在袖中紧握,指节发白。祖母的威压,如同无处不在的阴云,沉甸甸地笼罩着他。他仿佛能感受到长乐宫那道冰冷的目光,穿透宫墙,牢牢地钉在他的背上。登基之初的意气风发,此刻被一种巨大的憋屈和愤怒所取代。他是天子!却连用什么思想治国,都要听从一个深宫老妇的摆布!
“丞相先退下吧。”刘彻的声音听不出喜怒,带着一丝疲惫。 窦婴如蒙大赦,躬身退出。 殿内只剩下君臣二人——年轻的皇帝,和他最信任、也最为激进的支持者: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。此二人皆师从大儒申公,是“独尊儒术”和推行新政最坚定的鼓吹者和执行者。此刻,他们的脸上也充满了愤懑和不甘。
“陛下!”赵绾性子更急,上前一步,语气激愤,“太后干涉朝政,实非国家之福!黄老之术,抱残守缺,岂能应对当今天下之大变局?匈奴虎视眈眈,诸侯尾大不掉,民生凋敝,法令松弛!唯董仲舒之策,能立万世之本,开太平之基!岂可因太后一人之好恶而废此千秋大业?”他眼中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,以及对权力的渴望——一旦儒术独尊,他们这些儒生,便是新时代的掌舵人! 王臧也沉声道:“陛下,太皇太后年事已高,深居后宫,于外间之事,恐难尽知。陛下乃天子,乾纲独断,方为正道!儒术大兴,乃天命所归,大势所趋!若因太后阻挠而罢手,非但新政难行,陛下威信……亦将受损啊!”他的话更直白,点出了皇权旁落的危险。
刘彻霍然转身,眼中寒光闪烁!赵、王二人的话,句句戳中他的痛处和野心。威信?他何尝不想乾纲独断!天命?董仲舒的天人感应,正是赋予他这独断权力的天命神授理论!祖母的威压固然如山,但他体内流淌的雄心之血,却在炙热地燃烧!他需要一个突破口,一个能绕开长乐宫阴影的领域。
他的目光落在赵绾和王臧身上,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念头在脑中成形。 “卿等所言,不无道理。”刘彻缓缓开口,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决断的力量,“太皇太后深居长乐宫,颐养天年。朝中琐事,不必事事烦扰慈驾。”他刻意强调了“琐事”二字。 赵绾和王臧对视一眼,眼中燃起希望的火苗。 “立明堂、巡狩、改历诸事……”刘彻顿了顿,眼中锐芒一闪,“卿等可勿奏事东宫(长乐宫)!先行筹备,待朕旨意!”(让大臣不要向窦太后报告新政进展)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!年轻的皇帝,试图在重大礼制改革上,绕过太皇太后,秘密行事!他要强行推动新政,用事实迫使祖母让步,或者……等待时间。 “陛下圣明!”赵绾和王臧激动不已,俯身下拜。他们看到了冲破枷锁的希望曙光。
建元二年(前139年),春,长安暗流。
长安城的春寒料峭中,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正在积聚。皇帝刘彻在赵绾、王臧等新锐力量的簇拥下,顶着来自长乐宫的巨大压力,开始在有限范围内推行他的儒术新政。
未央宫石渠阁,被辟为临时的学术殿堂。董仲舒虽未被授予显赫官职(被刘彻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,远离中枢以避风头),但其思想已在皇帝周围的核心圈层中生根发芽。赵绾、王臧召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儒生博士,如精通《诗经》的辕固生、专研《尚书》的伏胜弟子等,在此讲论经义,考订典籍,按照董仲舒“大一统”和“天人感应”的理念,着手整理、规范和诠释儒家经典。空气中弥漫着竹简的墨香和激烈的辩论声。
“《春秋》大一统,乃天地之常!诸侯僭越礼制,便是逆天而行!” “灾异谴告,绝非虚妄!去岁关中大旱,蝗灾四起,必是上天警示!” “礼!乐!乃定尊卑、和民心之本!陛下当速立明堂,行巡狩礼,以正视听!” 年轻儒生们胸怀理想,言辞激切,充满了改造世界的热情。他们讨论的重点,已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,而是急切地想要将理论付诸实践——为皇帝设计巡狩的路线图、明堂的建造规制、新的历法草案、甚至商讨如何“改正朔,易服色”(改变历法和朝廷服饰颜色,象征新王朝的德运)。
与此同时,在长乐宫窦太后的授意和支持下,以丞相窦婴(虽内心矛盾,但不得不执行太后意志)、御史大夫直不疑为代表的老臣,以及众多信奉黄老学说的宗室、列侯,构成了强大的反对阵营。他们对新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充满警惕。赵绾、王臧等人“不奏事东宫”的举动,更是被解读为对太后的公然挑战和蔑视,极大地激怒了长乐宫。
“竖儒猖狂!竟欲隔绝内外,欺瞒太后!”一位白发苍苍的宗室老臣在朝会上愤然斥责。 “明堂?巡狩?劳民伤财,效法上古虚文,有何益处?” “灾异谴告?荒诞不经!将治国之责委于虚无缥缈之天意,要我等臣工何用?”黄老官员们嗤之以鼻。 暗流涌动,朝堂上的争吵日益激烈。赵绾、王臧依仗皇帝支持,锋芒毕露;窦婴、直不疑等则倚仗太后权威,寸步不让。双方势同水火,矛盾迅速激化。
风暴的降临,往往只需要一个导火索。而这个导火索,很快就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出现了。
长乐宫,太皇太后寝殿。
丞相窦婴跪伏在地,额角冷汗涔涔。他刚刚接到一份让他心惊肉跳的密报,不得不紧急禀报盛怒中的窦太后。 “姑母……不,太后……此事……此事非同小可……”窦婴的声音都在发颤。 “说!”窦太后枯瘦的手指攥紧了佛珠,声音冷得像冰。 “据……据可靠线报……”窦婴艰难地吞咽了一下,“赵绾、王臧……他们……他们暗中指使人……在长安市井散布流言蜚语……说……说……” “说什么?!”窦太后的声音陡然拔高。 “说……说陛下年幼,太后……太后妇人干政,牝鸡司晨……久居东宫,蒙蔽圣听……致使……致使天降灾异……关中大旱蝗灾……皆因……皆因妇人乱政,阴阳失调所致……”窦婴几乎是闭着眼睛说完的。
“轰——!” 仿佛一道无形的惊雷在窦太后脑海中炸开!她枯瘦的身体猛地一晃! “放肆!!” 一声凄厉到几乎破音的尖叫撕裂了长乐宫的宁静! 窦太后手中的紫檀佛珠串被她猛地扯断!光滑的珠子噼里啪啦地滚落一地!她枯槁的脸上瞬间涨成一种骇人的紫红色,因极致的愤怒而剧烈扭曲!胸口剧烈起伏,几欲窒息! “牝鸡司晨?!妇人乱政?!天降灾异?!”她每重复一句,声音里的怨毒和杀意就浓烈一分,“好!好一群狼心狗肺的逆臣贼子!好一个‘天人感应’!哀家还没死呢!他们竟敢……竟敢如此恶毒诅咒哀家!将天灾归咎于哀家?!离间我祖孙之情?!想要哀家死不成?!”
她浑浊的、早已失明的双眼,此刻仿佛要喷出火来,死死“盯”着虚空,声音如同诅咒: “查!给哀家彻查!赵绾、王臧!还有所有参与散布流言、诋毁哀家的儒生!一个都不许放过!哀家倒要看看,是谁借给他们一百个胆子!” 她的怒火,如同沉寂多年的火山骤然喷发!这已不仅仅是思想之争,而是赤裸裸的诅咒和逼宫!触及了她的逆鳞——权力和名誉!她要用最血腥的手段,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儒生,付出最惨痛的代价!
窦婴趴在地上,浑身冰凉。他知道,赵绾、王臧完了。皇帝也保不住他们。一场针对新政儒臣的血腥清洗,已在长乐宫的盛怒中拉开了序幕。
未央宫,宣室殿。
刘彻接到窦婴紧急求见的消息时,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当窦婴脸色惨白地将长乐宫得到的“流言”内容和太后的震怒转述完毕后,刘彻如遭雷击,僵立当场!
“蠢货!!”刘彻猛地一脚踹翻了身前的铜兽炭炉!滚烫的炭火和灰烬泼洒出来,殿内一片狼藉!他英俊的脸因极致的愤怒和一种被愚弄的屈辱而扭曲!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赵绾和王臧这两个蠢材,竟敢背着他,用如此下作、如此恶毒、如此致命的招数去攻击他的祖母!这哪里是什么“天人感应”?这是最卑劣的构陷!这是将刀把子亲手递给了他的敌人!这完全打乱了他的部署,将他置于极其被动和危险的境地!
“陛下!太后盛怒!已命张汤(时任侍御史,以酷烈闻名,是太后信任的爪牙)彻查此案!赵绾、王臧二人……恐在劫难逃……还请陛下……圣断……”窦婴的声音带着绝望。他深知太后的手段。
刘彻胸膛剧烈起伏,眼中闪过剧烈的挣扎。他欣赏赵绾、王臧的才干和锐气,他们是新政的急先锋,是他对抗祖母的重要臂膀。但是……他们愚蠢的行为,触犯了不可逾越的红线!祖母的报复,必然是雷霆万钧,若不牺牲掉这两个人,恐怕这把火会直接烧到他身上,甚至波及董仲舒和整个新政的根基!更可怕的是,一旦祖母以“不孝”、“受小人蒙蔽”的名义对他采取措施……后果不堪设想!
权力与现实,如同冰冷的铁钳,瞬间绞碎了他心中残存的情谊和犹豫。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,在窦太后积威数十年的阴影下,任何个人的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。 “立即拘捕赵绾、王臧!”刘彻的声音冰冷刺骨,没有丝毫温度,“交由有司……严加审讯!” “陛下!”窦婴惊愕抬头。 “去吧!”刘彻背过身,不再看他,声音疲惫而冷酷,“告诉太后……孙儿……御下无方……一切……但凭祖母懿旨处置。”这一刻,年轻的皇帝选择了隐忍和妥协,选择了丢车保帅。他知道,这不仅是放弃两个臣子,也是在祖母的威压下,暂时放弃了他独尊儒术的雄心。
诏狱。
阴暗、潮湿、散发着血腥恶臭的囚室。赵绾和王臧被剥去官服,换上赭色的囚衣,身上带着明显的刑讯痕迹,形容枯槁地被分别关押在相邻的囚室内。
“王兄!是我等太过操切,连累了你啊!”赵绾抓着冰冷的铁栅,朝着隔壁囚室嘶声喊道,声音充满了悔恨和不甘,“是我……是我一时糊涂,听信门客谗言,想以此流言……迫使太后放权……未曾想……”他痛苦地以头撞栏。
隔壁传来王臧嘶哑的苦笑:“赵兄……不必自责……董生言天人感应……我等……我等不过是……践行其道……欲为陛下……廓清君侧……咳咳……”他咳了几声,气息微弱,“只是……低估了……低估了那老太婆的手段……也……也未曾想到……陛下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。皇帝的舍弃,是他们心中最深的绝望和冰冷。他们曾视皇帝为希望,为知己,为可以托付理想的主君。然而,在太后的滔天怒火面前,他们的忠诚与理想,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沉重的脚步声在幽深的甬道中响起,如同死神的鼓点。时任侍御史的张汤,如同幽灵般出现在牢门外。他不过二十多岁,面容冷峻,眼神如同毒蛇般阴鸷锐利,带着一种对权力和酷刑的病态迷恋。他身后跟着几名面目狰狞的狱卒。
“赵绾、王臧,”张汤的声音平板无波,却带着刺骨的寒意,“尔等身为朝廷重臣,不思报效君恩,反行悖逆,散布流言,诬蔑太皇太后,离间天家骨肉,其心可诛!今证据确凿,尔等……还有何话说?”他手中捏着一叠厚厚的、沾着血污的“认罪”文书。
赵绾看着张汤那张年轻却如同恶魔般的脸,惨然一笑:“张汤,竖子成名!尔等酷吏,不过是太后的鹰犬!构陷忠良,屈打成招!我赵绾行事,或有过激,但忠心可昭日月!何罪之有?唯恨……唯恨不能见儒术大兴于天下!”
王臧也挣扎着站起,对着张汤愤然吐出一口血沫:“奸佞小人!今日是我等,明日便是尔等!这诏狱,迟早也会收了你!”
张汤脸上没有丝毫怒意,反而露出一丝古怪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:“死到临头,犹自嘴硬。尔等罪状,罄竹难书!太皇太后有旨:赵绾、王臧,大逆不道,赐——自尽!”他冰冷地宣判了结局。
狱卒打开牢门,将两只托盘扔了进去。托盘上,赫然摆放着两样东西:一杯色泽如琥珀、散发着淡淡苦杏仁味的毒酒;一段洁白的、象征着最后体面的——三尺白绫。
赵绾和王臧看着眼前的选择,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。死亡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们。但短暂的惊恐之后,是巨大的悲愤和绝望!他们满腔热血,欲辅佐明君开创盛世,却落得如此下场!
“陛下……陛下啊……”赵绾老泪纵横,仰天长啸,声音凄厉悲怆,“臣等……死不瞑目——!”他猛地抓起那杯毒酒,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!毒酒入喉,剧痛瞬间侵袭四肢百骸,他蜷缩在地,痛苦地抽搐,口中溢出黑血,眼中光芒迅速黯淡,最终凝固为无尽的愤恨与不甘。
隔壁囚室,王臧看着赵绾的尸体,发出一声凄凉的惨笑:“罢罢罢!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!张某!吾岂死于汝手?吾死于大义未伸耳!”他抓起那段白绫,奋力抛过囚室顶部的横梁,毫不犹豫地将头颈套入其中……身体悬空,挣扎了几下,便归于沉寂。
张汤冷漠地看着这两具尚有余温的尸体,嘴角勾起一丝残忍的快意。他挥挥手:“收拾干净。”然后转身,黑色的官袍消失在诏狱深沉的黑暗中。这黑暗,不仅吞噬了赵绾、王臧的生命,也暂时吞噬了刘彻“独尊儒术”的雄心。
建元二年(前139年),冬,长乐宫诏令。
赵绾、王臧被赐死的消息如同凛冽的寒风,瞬间席卷了整个长安朝堂。所有参与新政、鼓吹儒术的官员、博士,人人自危。长乐宫的铁腕,再次清晰地展示了她无可撼动的权威。
一道盖有太皇太后玺印的诏令,如同无形的枷锁,沉重地颁下: “自即日起,罢黜所有贤良文学之士!所属博士官,尽数免职!” “所有在建之所谓新政事宜,包括明堂、巡狩、改历、易服色等,一律停止!” “朝廷取士、治国方略,一切如旧,仍遵黄老无为之教!”
这道诏令,如同一盆冰水,将皇帝刘彻登基以来燃起的所有革新之火,彻底浇灭。未央宫石渠阁的讲论声消失了,年轻的儒生博士们被驱逐出宫,惶惶如丧家之犬。董仲舒虽因远在江都而幸免于难,但他那套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理论,在长安已成了无人敢公开提及的禁忌。
未央宫温室殿内,刘彻孤身一人。窗外寒风呼啸,殿内炭火再旺,也驱不散那种刺骨的阴冷。他手中把玩着一枚冰冷的玉珏,脸色阴沉得可怕。赵绾、王臧的尸体,祖母冷酷无情的诏令,像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他的心头。屈辱、愤怒、不甘……种种情绪在他胸中翻腾、冲撞,几乎要将他撕裂!
“董仲舒……”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,眼中燃烧着幽暗的火焰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……”这八个字,如同淬毒的种子,在他心底最深处,在失败的废墟和屈辱的灰烬中,顽强地扎根下来。他没有忘记董仲舒描绘的那个蓝图——一个思想统一、纲常有序、皇权至高无上的帝国!
他缓缓站起身,走到巨大的铜镜前。镜中映出他年轻而阴鸷的脸庞。他伸出手指,抚摸着冰凉的镜面。 “祖母……您老了。”他低声自语,声音冰冷而危险,带着一种近乎诅咒的平静,“时间……站在朕这边。今日之辱,朕……记下了。您能压得住一时,压不住一世!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……这大汉的思想,迟早只能有一个声音!那便是朕的声音!朕……等得起!” 镜中的年轻帝王,眼中闪烁着如同困兽般决绝而凶狠的光芒。暂时的蛰伏,是为了更凶狠的反扑。思想的战场,远未结束。独尊儒术的种子,已在权力的寒冰下,悄然孕育着破土而出的力量。它在等待,等待长乐宫的阴影散去,等待年轻的雄鹰真正掌握属于自己的雷霆。